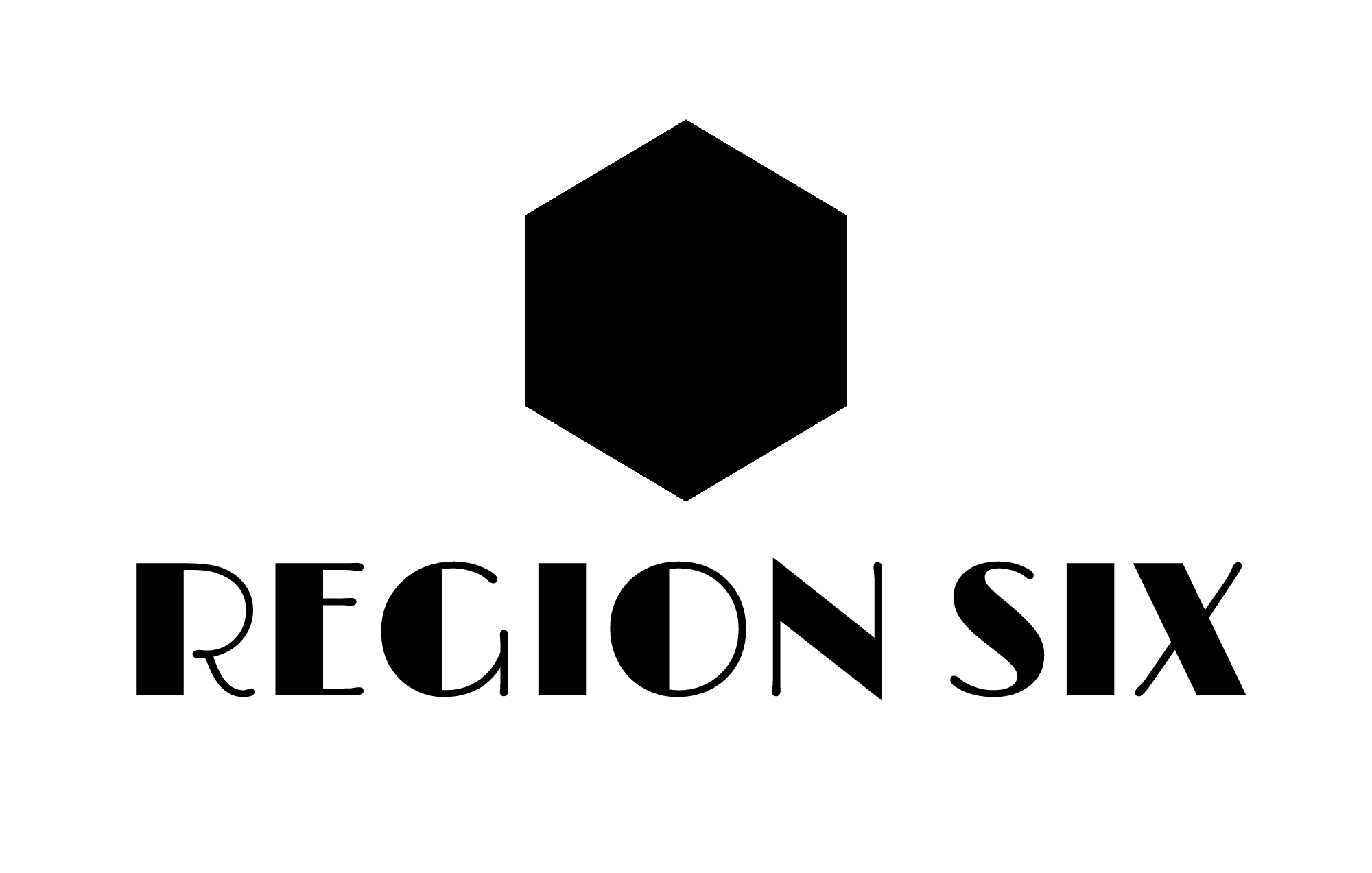果然做什么事到了第三次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转折。
九月底,第三次参加在科隆举办的前卫金属音乐节 Euroblast。前一晚先到达法兰克福。因为预热派对上换手环的最晚时间是十点,担心错过,于是就没有多做停留。头一回遇到中文说得这么溜的边检小叔。年轻好看工作人员还是那么多。突然开心了一点。我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在机场雇佣更多好看的边检人员,作为软实力的体现。要知道很多人在平日里完全没有机会被好看的人主动问那么多私人问题的。不过这绝非本人经验之谈。
边检小叔叔问我,你是去读书吗?(当然是用英文说的,他们中文应该还没有好到这种程度)。不是,就旅游。去哪里旅游?去科隆。去科隆干什么?去个音乐节。哪个音乐节?啊……一个很小的音乐节。你在乐队里玩音乐?不是,我是去看乐队的。你打算看哪支乐队?……在机场说可能有点不安全……我准备去看一支叫 Car Bomb 的乐队。
总是空荡荡的欧洲国际机场还是很让我不习惯,会怀疑是不是走错。边检和安检人员似乎是因为在某些时段没什么事干所以很“慢慢来”。之后在希思罗机场也遇到很搞笑的安检人员,觉得自己仿佛在一幕情景喜剧里。回来的路上忍不住想:同样是在机场工作,有些可以这么清闲自在,有些却像是在经受灵魂的拷打。
第一次注意到法兰克福有那么显眼的中文广告。火车站自动售票机还是那么不智能。折腾了半小时买好票,坐上驶往科隆的快速列车。阿姨来检票时,坐我身边的男生用屏幕碎成渣般的平板扫码。我忍不住问他车票花了多少钱。一听果然便宜了近三十欧。我埋怨了一下自己没有提前订票的行为,男生把平板硬塞进大背包,开始和我闲扯起来。
他是个口音像苏格兰人的瑞典学生,在读量子力学硕士。我这个外行人觉得很厉害于是兴奋得不行,而他却满是无奈和沮丧——他更喜欢做背包客到处旅行。对话让我想起许多处在那个年龄的年轻人,也包括曾经的自己。选了一个听上去很酷但难度很高自己也并不那么热爱的专业,可是也只能硬着头皮读下去。
但谁不喜欢到处玩呢?很多时候我们没办法选充满快乐的人生,只能选有意义的人生。从进化的角度来看,人类存活的原因本来就不是为了快乐。导致快乐的行为主要都是为了能更好地传宗接代。如果是活着是为了快乐,大家就都会去嗑药,然后在二十一岁就死掉。
窗外一片漆黑,车厢里是尿色的灯光。等接近科隆火车站时,我才发现这个瑞典男生长得简直和年轻时的 Ryan Gosling 神似。可能再高瘦一点,胡子再浓密一点,外加一副黑镜框。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像缩减了一半。下车时我差点把行李忘了。
科隆飘着小雨,也比预期的冷了不少。去酒店时又碰上了巴士自动售票机的问题,硬币投不进去。“那怎么办?我没有面额小的纸币了。”胖墩墩的阿拉伯裔司机小哥抽着烟走上巴士瞟了一眼说:“哦,那你很幸运!”挥挥手叫我别付钱了。
到酒店入住时已经九点半。看看雨,感受了下自己的头发质感和身体气味。想想还是不去预热派对了。于是站在酒店门口一个人就着烛光喝欢迎酒,观赏人类。当时的情绪很矛盾,好像特别庆幸,折腾了一路总算到了。好像觉得,终于要开始了!但其实又已经在为离别做好心理准备,有点伤感。
后来听说预热派对并不怎么样,不过手环过了十点还是有人帮你换的。派对原先的场地 Underground 是科隆很具标志性的音乐场地,但就和许多曾存在于没有灵魂的国际化的城市里的文化场地一样,最近被关掉了。新场地构造不科学,吧台旁边当时是一个很傻的说唱比赛,楼上才是预热演出。许多来预热的人不想听说唱又要喝酒,就干脆直接呆在门口了。
我住的酒店在热闹的 Heumarkt 附近。这样无趣的天气里依旧有许多人在餐厅外大声聊天谈笑。喝着喝着,一个戴金边眼镜,穿灰色卫衣的矮叔叔指着我的牛仔裤说,你是发生了什么意外把裤子撕破了么?我心想这个搭讪方式有点烂,但还是说,对啊,下雨路滑,摔得不轻呢。叔叔似乎有些醉,但耍贫嘴的时候反应又挺机敏的。
原来他已经去过上海二十多次,去过的中国城市比我多得多。我就叫他 P 大叔好了。我们从旅游聊到工作。我发现他开玩笑的方式甚至笑声都和我的一个朋友非常非常像。是个尽管看起来很不正经但阅历挺丰富的人。不再经商后他把主要的时间都花在海上航行。
“但我也工作啊!发发邮件,打几通电话。每个礼拜要工作三四个小时!”
我不可避免地提到了海洋里塑料的问题。他也不可避免地谈到了吃各种动物的经历。
“反正现在吃什么都会吃到塑料微粒”,我说。
“对,吃塑料嘛。我最喜欢吃黄色的那种塑料!哈哈哈!”
快十二点时我实在困得不行,便要和他道别。P 大叔的一帮朋友就坐我们旁边,我觉得这么“占用”他也有点不好意思。离别前他和我说:我有个意大利朋友,叫安东尼,在学禅学之类的。我觉得值得你认识一下。附近有家越南餐厅有很棒的素食,我们明天一起去吃午饭吧。
我以为他会介绍一个对中国文化很了解又吃素的意大利帅哥给我。到了中午,他们来酒店接我。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头发花白比 P 大叔年纪还大点的大叔。站在一辆挂着红色 Freitag 挎包的纯黑自行车旁。
我们一路走过繁忙的商业街。P 大叔抱怨,说自己的好看的车铃昨晚被人卸掉了,决定自己也要去偷一个。走着走着,快接近一个街头弹唱的男青年。安东尼看上去若有所思,操着口音浓重的英语缓缓说:“近距离的音乐表演总有一种特别的魔力,对不对?就算演的音乐听上去跟屎一样。”
安东尼在研究侧重于文化的人类学。似乎是把我当作研究对象了。问了我不少文化和政治方面的问题。我也假装自己很懂语言学什么的,毕竟读的两本 Steven Pinker 的书还没有完全忘掉。P 叔负责在期间插科打诨。好在这顿午餐是免费的,对话也算有营养。
吃完因为赶车便和他们匆匆道别。去场地的列车上,发现坐我对面的两个小哥也去音乐节。大家今年都不是第一次去了,但还是一起成功地下错了站。第一年去 Euroblast,我也在路上认识了两个北欧女生。这次则是一对从巴黎来的兄弟(长得一点儿也不像)。有缘分的是,我们还一起呆到了音乐节的最后。
门口检包的姐姐认出了我,给了我一个超级亲切淳朴的笑容。从舞台传出来的共鸣声,空气里那种属于 livehouse 的特殊潮气。开始觉得浑身都很舒服放松,开始觉得有点激动了。这应该就是让许多主办方和乐迷都欲罢不能的感觉。还有和朋友在异地重逢叙旧的期待和喜悦。 一年的时间确实过得非常快。真是人越老,时间就越觉得快。
这届 Euroblast 请到了不少澳大利亚乐队。悉尼的 Lo! 有个肢体和表情很戏剧化的主唱(类似不那么娘炮的 George Clarke)。上身布满纹身,脱臼了一样来回移动肩胛骨,配合相当凶猛的音乐,又加入了我很喜欢的 sludge 元素,是第一个惊喜。
珀斯的 Voyager 今年发行了一张很棒的专辑。女吉他手 Simone Dow 在台上很抢眼,让我想到去年看到的 Aliases。能有台风潇洒而且技术超级过硬的女成员真的很给乐队加分。演到中间,乐队还来了一段快速的电子舞曲改编,非常有意思。长发飘飘的主唱唱功了得,老练程度不愧是组建了十多年的乐队。
音乐节第二天撞见他时本来只想快速地打个招呼,没想到他还挺健谈的,和我们聊了来。一起称赞那天刚演完的 Circuits of Suns——另一支今年特别大的惊喜;自嘲他的全职工作——原来是正儿八经的律师,拥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还打开手机给我们看他的官网。主页上的他一脸凝重,大金发梳得油亮扎起来放在后边,穿着一套笔挺的西装。他们的专长是移民法,所以经常和中国人打交道。他会讲几句不赖的中文,对红包之类的文化也十分了解。
第二天的压轴,期待很久的 Twelve Foot Ninja 反倒没让我太惊喜。尽管大家都跳得很欢乐,而且音乐节结束后的官方评选里他们也是人气最高的。主要演了新专辑的歌,而且成员也没有像 MV 里头那么有喜感。我想象中会有很多互动来着。对了,Uneven Structure 看得也不是太爽,演得全部都是新歌。新专辑的水准么……大家都心知肚明的。
或许是因为在他们前面演的 Car Bomb 能量太惊人,对于我来说,任何之后出场的乐队都会被抢掉风头。最超出预期的是 Sleepmakeswaves,因为先前知道 Euroblast 会请他们,所以没在上海看。如果早些知道现场可以这么重型我不介意多看几遍的。演出的后半段 Sleepmakeswaves 散发出的能量,以及更接近 post-metal 的转变超级过瘾。
印象很深刻的还有 Angel Vivaldi。关注他好多年终于第一次看到本尊。实力和舞台表现力都非常强,但可能不会讨一些直男的喜欢。因为有些“太显摆”了。我看过的吉他 solo 艺人演出很少,以我有限的见识来讲,他比我最近一次看的 Nick Johnson 演出观赏性高出太多了。不过 Angel Vivaldi 是以乐队形式演奏这样比较有点不太公平。琴弦像和他手指长在一起,能一边弹奏一边按手机给我们拍照,一边演一边喝水……反正我看完是觉得无以伦比,但几个男性朋友都对其不屑一顾(嫉妒)的样子。我晚上还不小心梦到他了。
Circuit of Suns 是第二天头一支在副舞台看到的乐队。副舞台下午人总是很少,加上舞台很低,所以我遇到喜欢的团总会站在最前面。吉他手戴着 Car Bomb 的帽子,弹奏的音乐也非常接近——我后来才知道他们正在和 Car Bomb 一起巡演。他们像是在光谱上更接近死金那头的 Car Bomb。十分有煽动性的黑人主唱也为 Circuit of Suns 增加了同类乐队没有的独特唱腔(想象一个不 gay 的 Chino Moreno)和表现方式。非常棒,强烈推荐。他们 2015 年的同名专辑在 Bandcamp 上是自由定价的。
可能是因为我看得很认真很享受。演出结束后吉他手朝我一伸手,直接把拨片给了我。傍晚我一个人在副舞台歇息的时候,他突然从黑暗中冒出来,问我衣服大小是几号,然后就不见了。没过多久又出现在我面前,一把将乐队的卫衣塞进我手里,我道完谢他就又不见了。这让我想起去年看 Verderver 的场景,这种乐队事业初期时对乐迷怀抱的感激真的是挺可爱的。
不过这不是那天的最大亮点。傍晚的时候,我正一个人捧着刚买的炒面(在外国吃炒面的理由:音乐节少数性价比还能勉强接受的素食)走向副舞台。突然,距离我差不多五米远的地方有人说了句”Nice shirt!” 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和我说的(我当时穿了件现场没有卖的 Car Bomb 卫衣),但还是下意识朝那个方向看了过去。
发现几个小叔笑眯眯地在看着我。我飞快地试图辨认他们衣服上的乐队名字但失败了。于是只好说:“你们也是来看 Car Bomb 的吗?” “我们就是 Car Bomb 啊。” 我当时简直难以置信,他们又给我看腰间挂着的艺人牌。我立即把炒面随手一放进入迷妹状态。“我们叫你,可你完全无视我们了”。我又激动又尴尬:“我这不是一心想着我的炒面嘛……不好意思我很少搜乐队的照片,所以认不出你们!”“没关系,没人认得出我们!”
这种关键时刻当然要甩出“我是从中国来的”这张地域牌了。我说我这次来主要就是来看你们的,当然也是特别想看 Devin Townsend 的。他们说 Devin Townsend 是很厉害。巡演经纪马上招呼我们来两张合影,最后还把这张照片放脸书什么了。小叔都很会做表情摆 pose,超级可爱。我只会尬笑。
拍完照小聊了一会儿,他们要回后台:”你的面都要凉啦!““我现在才不在乎那碗面呢!”
吃面的时候,我遇到当志愿者的朋友,他很激动地和我说“怎么回事,为什么我听到 Car Bomb 在提到一个从上海来的姑娘!?”我后来听他说,Car Bomb 称得上是这批阵容里最随和,最不挑剔的乐队了。觉得自己品味特别好!另一个比较难忘的瞬间是,在 Frontierer 要上台前我又遇到 Greg,问他“你遇到年轻的乐队听上去和你们一样是什么想法?”他笑着说:“觉得非常荣幸。”
最后一天 Devin Townsend 演完我也冲到前面和他握手了(料想自己当时一定异常笨拙有失雅观),他竟然还记得我(去年10月曾在上海短暂地和他聊过)。之后,我还在寒风里和一个奥地利男青年一个法国男中年(都非常宅男的样子)一起等他们等了至少 45 分钟。我心想,难道我的内心世界和这些宅男是相似的吗?
接近凌晨,最先从后台出来的,我忘记是吉他手还是鼓手了,非常亲切地和我们聊天。我问他,唐老师的即兴段子这么多,你们是怎么知道哪里开始 cue 音乐的?“我们就是知道,演多了就有那种默契了呗。”
在冷风里等了很久,唐老师拖着疲惫的身躯戴着帽子低调现身了。和舞台上充满精神气的样子反差极大,看得出他每次演完真的是累坏了——如果 Car Bomb 的现场是像 Mad Max 5 那样一气呵成酣畅淋漓的动作片,那 Devin Townsend Project 就是 GotG 那样的科幻太空史诗喜剧。即便是很疲惫,唐老师还是在巡演巴士旁一一满足粉丝的要求,聊天、合影、签名:“你们还有啥要我签的吗?”一个女孩递给他一盒牛奶,说:“我没东西可以签了,能不能在我的牛奶上签个名?”“当然没问题!”
我忍不住再次觉得自己的品味特别好。
再见 Textures
这大致就是我的“意想不到的转折”了。倒也不是说先前两次没有“转折”或者不够有趣,而是这回达到了自认为的乐迷顶点。音乐节最后一天也遇到了人生很难得的经历。和有趣的朋友呆在一起,发生了让我事后觉得相当 meta 的对话,还带了个冰岛的男生回酒店了——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精彩——冰岛男生是迫不得已寄人篱下的,我只是帮个忙。在雨夜里暴走了四十多分钟回到酒店,路上他还和我讲了中国游客在他们的森林里大便的事情,让我觉得难以置信。因为不习惯有个醉醺醺的男生睡我旁边,我几乎没闭过眼,还被他用手臂甩到了脸上。总之,是人生很难得的经历……不过,有好事发生也意味着有许多遗憾,虽然我不是 Textures 的老粉丝,但告别演出还是挺伤感的;虽然见了几个老朋友,但也没有像预期那样聊很久或者出去吃饭。毕竟新朋友英语更好一些,哈哈。